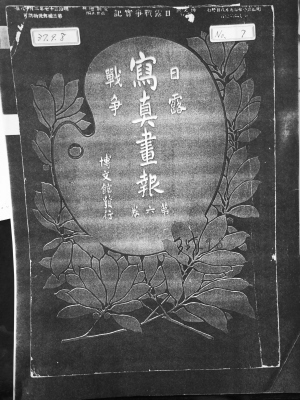| 鲁迅“弃医从文”另有真相? |
| 鲁研领域抛出一个新说法:这是鲁迅对现实的一种妥协 |
| 2018年07月18日 08:54:20 |
| 来源:绍兴网-绍兴日报 |
|
鲁迅“弃医从文”事起“幻灯片事件”,我们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就读到过,鲁迅年表和文学史中对此皆有记载。因为其重要的转折性,“幻灯片事件”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近日,《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上刊发了年轻学者王国杰的论文,他对“幻灯片事件”提出了质疑,并认为鲁迅“弃医从文”的根本原因或是向现实妥协…… “我们总是把鲁迅当作意志超常者看待,忽视了他平凡的一面,其实鲁迅也是从一个普通人成长起来的,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鲁迅并非有超乎常人的异禀,同样是从现实中摸索自己可能的出路。”王国杰说,将其放回历史背景中去考量,对年轻人面临选择时更有启发意义。
《日露战争写真画报》封面。 新说 “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很大原因是迫于现实。” 抛出这一观点的是安徽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老师王国杰。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编辑的牵线下,记者与王国杰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位“80后”鲁研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文学。 “鲁迅是现代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此前,对《呐喊》《彷徨》等进行研究的学者众多,所以我将研究重点放在《朝花夕拾》上。在细读《鲁迅全集》后,结合日本鲁研学者的文献,我提出了这一观点。”王国杰在电话中,向记者讲述了他选题的由来。 鲁迅“弃医从文”,各种传记都认为是受“幻灯片事件”影响。而王国杰细读《鲁迅全集》时,特意留意了相关说法。“可以看到,鲁迅至少有四次提到过这一事件。” 在这四处的描述中,王国杰发现了矛盾之处:第三次说是枪毙,其他几次却说是斩首;第一、第三次说有中国人围观,第二、第四次却没有。 “这四次回忆中都说得很明确,‘幻灯片事件’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即从学医转而倡导文艺。但是,除了鲁迅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因为当时鲁迅是仙台医专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而这件事他此前也未对朋友说起过,况且思想转变是内在的,旁人也不能窥视出来,所以他的回忆也就成了孤证。”王国杰说。 从日本鲁研学者处,王国杰还发现,渡边襄曾经查看过东北大学(原仙台医专)医学系细菌学教室里保存至今的日俄战争幻灯原版片,原来总共是20张,现在还剩下15张,在这些尚存的幻灯片中并没有鲁迅所说的场景,而且渡边襄推测,即便是在已经丢失的幻灯片中,“有处死俄探画面的可能性似乎也很小”。 渡边襄的所有材料考证都指向一个观点,即鲁迅所说的幻灯片很可能不存在。但是,渡边襄考察了当时的新闻报纸,发现其中常有关于中国人做俄国侦探而被日本人杀害的报道,“有关处死中国人俄探的记录,作为新闻报道、插图等刊登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可以认为,鲁迅在仙台医专期间对这些是有所见闻的”。这似乎在暗示我们,是鲁迅把报纸新闻错记成了幻灯片。 王国杰明确表示,研究这些细节,并不是要说明鲁迅在“撒谎”,而是想说明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抉择,固然与“幻灯片事件”相关,但也不完全是因此而发生。鲁迅强调“幻灯片事件”对自己思想转折的影响,目的是强化自己人生的戏剧化效果。 王国杰认为,我们要从鲁迅的性格分析其行为选择的特点,关注现实境况对于青年鲁迅人生选择的影响。青少年时期的鲁迅尚不具备中年鲁迅那种强大的意志,向现实妥协是鲁迅“弃医从文”更为合理的解释。
《日露战争写真画报》内页。 求证 深度了解一个人,必须将他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了解,鲁迅亦不例外。 王国杰在论文提到,关于鲁迅的性格,学界往往强调他与现实决然对立的一面,却少有人谈及他向现实妥协的一面。 回顾鲁迅的人生历程,并不缺乏向现实妥协的例子。比如,鲁迅遵从旧式为祖母送葬;戴上假辫子迎娶母亲为其定亲的妻子朱安;因为省钱,去读了不用学费的南京水师学堂等。 鲁迅曾经选择医学专业,有冲动的成分。他在选专业时认为,新的医学对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这表明鲁迅不是对医生这个职业有所向往,而是对这个职业在日本曾产生的历史作用有兴趣,只是后来进了医科学校才发现,学医并非自己当初想象的那样。 1904年8月,鲁迅进入仙台医专学习,29日他就给好友蒋抑卮写信,对医学课程表达了强烈的反感,“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这封信足以说明医学难以激发鲁迅的兴趣和热情,但他仍然坚持了两年,直到1906年才退学,原因就是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退学。 是什么让他下定了决心呢?王国杰认为是现实的逼迫。1903年清政府正式公布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中规定:“在日本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八年),给以举人出身,分别录用。” 仙台医专就属于高等学堂类,按照这个章程要求,鲁迅必须以优等文凭毕业才能获得举人出身,而鲁迅第一学年的成绩平均分是65.5分,在142名学生中排名第68位,这个成绩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想达到优等也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他毕业回国后,被认定为举人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鲁迅处于这种痛苦的境遇:一方面他不喜欢学医,另一方面即使学成毕业,回国后也没有就业前途。于是,鲁迅就像当年放弃科举一样放弃了学医,这个选择是鲁迅面对现实境况的无奈,也是对现实的妥协。 理性意志终究敌不过天赋本能,鲁迅选择弃医从文,除了启蒙的因素之外,对文艺的“兴趣和爱好”也是重要因素。 正如当下著名写手冯唐,本该留在北京协和医院的肿瘤科里治病救人,那是妥协于其父母的安排,但他实在扛不住不断膨胀的写作欲望,遂而成了著名作家。 当下年轻人,在选择专业或求职时,可能会首选热门专业或高薪职业,那也是对当下的妥协。然而,最终想要取得突破性的成就,还需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即便伟人也不例外。 反响 “‘幻灯片事件’导致鲁迅‘弃医从文’已是难以颠覆的定论,王国杰先生的论点是一家之言,但可以讨论。”绍兴鲁迅纪念馆原馆长裘士雄在得知新论点后认为,鲁迅离开仙台医专后,去了东京,和中国留学生一起筹划名为《新生》的刊物,以及此后他所走的生活道路,都在验证着他“弃医从文”的主动性,而并非被迫妥协之举。 “王国杰论文中提及的日本鲁研学者渡边襄,是与我同龄的朋友,我们的交流不少,他研究鲁迅,也是中日友好派人士。多年前,我也曾托日本的李冬木给我寻找一些有关‘幻灯片事件’的资料,当时他专门给我复印了一些。”裘士雄一边说,一边向记者展示了一叠复印资料。其中资料的首页是《日露战争写真画报》封面,裘士雄解释:露是指俄罗斯。那是一本日俄战争的照片报道集,其中一张照片上,确实如鲁迅曾经描述“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不同的是照片由于裁成圆形,无法看清是否有人围观。 “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时,他们的电化教育非常普及,所以课堂上很可能有老师给他们放过,也可能是鲁迅先生在报道中读过。所以,我仍坚持鲁迅自己多次所说的观点。”裘士雄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此,绍兴另一位鲁研学者认为,鲁迅研究存在写实与写意,一味写实,研究到头发丝之类,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了。 记者还将王国杰的论文,发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他阅后认为,这篇论文综述近年多位鲁迅研究者的成果,有一定的道理。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的鲁研专家曹禧修教授是这篇论文的外审专家。他认为,近年来陆续有此类观点出现,但这篇论文比较客观、集中、整体地反映了新观点。 “我们首先要肯定鲁迅是一个伟人。他‘弃医从文’的经历是很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但他的伟大不是因为政治因素。他是一个人,不是神,是可亲、可敬的普通人。他年轻时经历过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会经历的选择,不能排除现实的推动作用,真切地还原将更加体现他的伟大。”曹禧修说。 鲁迅成为钢铁战士,心智必定经过百般磨练,他是如何变得强大而坚韧的,希望有更多的学者通过研究来真切还原。 新闻助读 鲁迅作品四次提及“幻灯片事件” 第一次是《呐喊·自序》中的讲述: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段文字是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之前,他回顾了自己前半生的思想轨迹后为小说集所写的序言,时间是1922年12月3日,发表在第二年的《晨报·文学旬刊》上。 第二次讲述是1925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道: 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 第三次提到是在1926年,鲁迅集中撰写了10篇回忆散文,后结集为《朝花夕拾》,其中的《藤野先生》这样描述“弃医从文”事件: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第四次是1930年,鲁迅在《鲁迅自传》中写道: 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 (摘自《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
| 作者:记者 潘晓华 编辑:陈文华 |
| 绍兴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① 凡本网注明“稿件来源:绍兴网(包括绍兴日报、绍兴晚报)”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稿件,版权均属绍兴网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本网协议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表。已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下载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绍兴网”,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 ② 本网未注明“稿件来源:绍兴网(包括绍兴日报、绍兴晚报)”的文/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下载使用,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稿件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如擅自篡改为“稿件来源:绍兴网”,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如对稿件内容有疑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③ 如本网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在两周内速来电或来函与绍兴网联系。 |